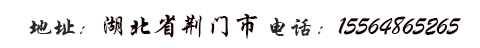恐怖的假设问题蘑菇中毒病例和ldqu
|
昆明白癜风治疗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769963.html鉴于苏州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会议主办方决定会期由原来的3月23日-24日延至3月30日-31日,会议日程不变,地点仍在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 让我们从死亡的边缘学会生命的真谛。 Letuslearnfromthelipsofdeaththelessonsoflife. -FelixAdler, PhotobySangharshLohakareonUnsplash 1细思极恐的假设问题《Whatif?: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书中搜集了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假想问题:如果地球停止自转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的打印机可以打印出真的钱,对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影响?你从多高的空中往下扔一块牛排,它到地面的时候才会被(因空气摩擦而产生的热量)做熟了?作者RandallMunroe根据物理、化学、生物、经济等学科的知识对每个问题给出了详尽的解答。这些问题问得天马行空、匪夷所思,回答得妙趣横生、有理有据,既引人思考,又让人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图1.《Whatif?: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的封面 图源:6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DNA突然消失了,他会再坚持多长时间?读到这个问题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觉得空落落的。DNA承载着一个人的全部遗传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剧本。丢掉了这个剧本,我还是我吗?作者评论道,当一个人失去所有的DNA时,他的体重会立刻减少约三分之一磅(约克)。当然,他并不推荐这一减肥策略。能做到体重同样迅速变化的还有更好的办法:尿泡尿、捐次血、理理发等等。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体内的全部DNA突然消失了,他会无暇顾及“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和体重下降现象。他将经历痛苦的、不可逆转的、(相对)漫长的死亡过程。在6-12个小时内,他不会感到任何异样。但在度过这段平静期后,他就会开始恶心、呕吐。这是因为体内原本生长活跃的细胞由于DNA的缺失而停止分裂。而生长活跃的细胞主要分布在消化道、骨髓和发囊里。由于得不到新的细胞的补充,在后续的几天中,肠壁会变得千疮百孔,大肠里的细菌和其它微生物会进入到血液和组织中,同时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会被耗尽,引发全面感染。但受害者可能没有机会等到那个阶段——DNA消失带来最大的毒性将在12-24小时内全面爆发。如果说DNA是生命的硬盘(harddrive),那么RNA则是软件(software),蛋白就是硬件(hardware)。每个细胞的正常运作都依仗于数千种蛋白的功能。DNA消失后,转录(从DNA到RNA)立刻停止,不会再有新的RNA产生。翻译(从RNA到蛋白)的中止会有些滞后——需要等到残留的mRNA和tRNA大部分被降解完。因此,细胞里和组织内的mRNA和蛋白不会立刻消失。mRNA在体内的半衰期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而蛋白的半衰期则跨越数小时至数天,但它们的储备终将耗尽。随着越来越多的蛋白被降解殆尽,越来越多的细胞、组织、器官将出现功能紊乱,直至多系统衰竭,最后死亡。当然,一个人的DNA的突然全部消失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所以我们无法完全准确预测受害人的真正发病、死亡历程。但DNA消失的部分后果可以被一些药物、毒素的作用模拟出来。观察它们的副作用或毒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比如,大部分化疗药会杀死生长活跃的细胞,它们的副作用可以用来模拟细胞停止分裂带来的毒性:恶心、呕吐、脱发、疲劳和免疫力下降等。而mRNA和蛋白合成被终止的毒理过程可通过一些误食剧毒蘑菇的病例来观察到。2蘑菇中毒事件年的一天,住在美国波士顿郊区的一位72岁的讲俄语的妇女看到她家附近的人行道旁长出了很多蘑菇,不禁喜出望外。这些蘑菇戴着灰米色的伞帽,形状和她很久以前在乌克兰家乡经常吃的一种蘑菇很像。她采摘了整整一袋子蘑菇,到了晚上连煮带炸,做了几个蘑菇菜肴。9点左右她美餐了一顿——这些蘑菇太好吃了,让她想起了家乡的味道。一夜无事。第二天早晨,她45岁的儿子来看她,在8点左右也尝了一些蘑菇。到上午11点,母亲把剩下做熟的蘑菇也吃光了。下午1点,母亲开始出现呕吐、腹泻、右上腹疼痛等症状。到晚上10点,儿子也出现同样的症状。母子二人意识到那些蘑菇可能是有毒的,在夜里11医院就诊。母亲的其它生理指标都正常,但血液中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丙氨酸转氨酶(ALT)的水平远远超出正常生理浓度范围,标志着肝脏受到损害。她的儿子除了升高的ALT和AST水平外,还出现了心跳过速。医院里,两人吞服了50克活性炭(AC),并静脉注射了N-乙酰半胱氨酸(NAC,mg/kg)。活性炭的作用是吸附肠道中的毒素,而NAC被认为可以减少自由基损伤,保护肝细胞。次日凌晨3点,两人被转移到具有肝移植能力的急救中心。在急救中心,两人又被肌肉内注射了高剂量(万单位)的青霉素,并口服了毫克的水飞蓟宾(silibinin)。使用两种药的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阻止蘑菇毒素进入肝细胞。在母子住院的第二天,他们的家人把一些剩医院。经毒物控制中心的真菌学家鉴定,这种蘑菇属于赭鹅膏(Amanitaocreata)。图2.母子俩误食的毒蘑菇。 图源:8 转院后,两人的AST和ALT的水平继续飙升。在食用蘑菇后第60个小时,母亲的AST和ALT都超过了(IU/L),而正常生理水平应为15-35。儿子也在食用蘑菇后第60个小时达到峰值——ALT为,AST为。除了活性炭、NAC、青霉素和水飞蓟宾外,母亲还注射了西咪替丁(cimetidine,常用于抑制胃酸分泌,来自动物中毒实验的数据表明它可以减少肝细胞坏死和线粒体损伤),服用了大量的奶蓟草提取物,并输注了新鲜冷冻血浆。在连续5天水飞蓟宾输液后,母亲的AST和ALT水平开始向正常水平回归。住院8天后,母亲基本恢复正常,办理了出院手续。由于儿子吃的毒蘑菇量不大,他第6天就出院了。需要指出的的是,除了活性炭外,他们接受的所有治疗和药物都是实验疗法。针对鹅膏菌中毒还没有建立起标准的、可靠的治疗程序。母子俩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如医院,并告诉医生自己可能是蘑菇中毒,他们很可能会丧命。如果没有任何治疗和处理,误食赭鹅膏或其它鹅膏菌的人会经历四个阶段:潜伏期(8–12小时)、胃肠炎期(8–48小时)、假愈期(48–72小时)、和内脏损害期(72–96小时)。最为恐怖的是假愈期——这一阶段中毒者感觉良好,好像彻底痊愈了,但实际上他们体内越来越多的细胞在消耗最后的储备蛋白,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母子俩错把赭鹅膏当成了故乡的橙盖鹅膏菌(Amanitacaesarea)。橙盖鹅膏菌是无毒的,主要分布在东欧和北非,而在美国没有。这起中毒病例绝不是孤立事件。年,俄国裔的三口之家在旧金山湾区爬山时也误食毒蘑菇。在同一年,美国共有96人因误食鹅膏菌而丧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近年来随着乌克兰移民的增加,蘑菇中毒事件也越来越多。赭鹅膏与橙盖鹅膏菌最主要的差别是,赭鹅膏含有鹅膏毒素(amatoxin),而橙盖鹅膏菌则没有。图3.有毒的毒鹅膏(Amanitaphalloides,左图)和无毒的橙盖鹅膏菌(Amanitacaesarea,右图)。 图源:8 3鹅膏毒素世界上95%的蘑菇中毒致死事件是由蘑菇中的鹅膏毒素造成的。鹅膏毒素包括至少9种结构类似的毒素,其中研究最广泛的是α-鹅膏菌素(α-amanitin)和β-鹅膏菌素(β-amanitin)。它们具有由8个氨基酸构成的双环结构。图4.α-鹅膏菌素(α-amanitin)和β-鹅膏菌素(β-amanitin)的分子结构。 图源:9 鹅膏毒素能够高度抑制真核细胞里的RNA聚合酶II,而RNA聚合酶II负责合成mRNA。一旦鹅膏毒素进入细胞并结合RNA聚合酶II后,该细胞的mRNA合成能力会降低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鹅膏毒素的毒性能模仿DNA突然消失的后果。鹅膏毒素是迄今人类知道的唯一一种RNA聚合酶II抑制剂。鹅膏毒素具有高度水溶性,这导致它们不能被动地扩散进人体的大多数细胞。但它们能结合肝细胞表面的一类特殊受体(OATP1B3),从而被内吞进肝细胞。因此,肝脏成为鹅膏毒素的主要靶器官。此外,鹅膏毒素主要是通过肾脏和泌尿从体内排出,它对肾也有很强的毒性。从这点上来说,鹅膏毒素的毒性并不能完全复原DNA毁灭的后果——后者会导致体内所有细胞同时失去合成新的mRNA和蛋白的能力,其表现的毒性要更严重、更广泛。自40多年前被发现后,鹅膏毒素被广泛应用在科研上,成为一个研究基因表达、转录调控的工具。自然界的很多毒素都曾被人类开发,成为科研工具,甚至转变成治病的良药。鹅膏毒素能否也在治疗疾病方面发挥作用呢?答案是:有可能。图5.从毒素到药物:如今临床上使用的许多治疗药物都起源于动植物或微生物产生的蛋白/多肽毒素。这里给出三个例子。 4魔术子弹魔术子弹(magicbullet)是德国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保罗·埃里希(PaulEhrlich)于年提出的一个科学概念:就像一个魔弹一样,理想的药物应该特异性地杀死病菌,而对人体细胞没有任何影响。埃里希当时主要在各种染料中寻找魔弹——如果一种染料能够特异性地染色(进入)细菌或病原体,那它就有可能被改造为魔弹药物,或者变成药物的载体。魔术子弹的概念在21世纪崛起的一类抗癌药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抗体-药物偶联物(ADC)。ADC药物分子由三部分组成:抗体、连接子和偶联的小分子化学药物。抗体相当于子弹头,能特异性地瞄准、结合靶细胞;而其携带的小分子药是效应分子,被内吞到细胞内部并和抗体分离后会杀死肿瘤细胞。小分子药在从抗体身上剥离前并没有杀伤性。我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当肿瘤细胞遇见ADC时,它会放声歌唱:“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第一个ADC药物(辉瑞的Mylotarg)于年被美国FDA批准上市,迄今在美国已有11种ADC药物获批。ADC中的小分子药物往往毒性很强,单独作为抗癌药副作用太大。但抗体的引进增加了其靶向性和安全性。鹅膏毒素毒性更大,无法单独用药。我们能否把它们和抗体偶联,让它们作为ADC药物中的效应分子而发挥作用呢?德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HeidelbergPharma正在开发以鹅膏菌素为基础的抗体偶联药物(简称ATAC)。图6.ATAC分子结构模型。红色部分为改造过的鹅膏菌素。 图源:12 与其它的ADC药物相比,由于鹅膏菌素独特的作用机理,ATAC药物有四个潜在的优势:1.ATAC既可以杀死快速分裂的细胞,也可以杀死处于休眠状态的细胞。传统ADC效应分子的杀伤作用是通过造成DNA损伤,或者破坏微管网络来完成的。而这两种机理对处于非分裂状态的肿瘤细胞(比如某些肿瘤干细胞)则无效。而鹅膏菌素一旦被输送进肿瘤细胞里,不管细胞处于何种状态都能大开杀戒。这便于ATAC药物对肿瘤细胞斩草除根,不留后患。2.某些癌症对ATAC尤为敏感。抑癌基因TP53的功能缺陷在癌症中非常普遍。在很多肿瘤中,TP53的功能下降是由17号染色体丢失了携带TP53基因的片段(del(17p))造成的,而缺损的染色体片段往往也包括RNA聚合酶II的基因(两个基因相隔只有kb)。和正常细胞相比,这类肿瘤细胞的RNA聚合酶II的表达减少了一半,所以它们对鹅膏菌素的杀伤作用更敏感。这和近年来非常热门的“合成致死”用药机理有些相似:肿瘤细胞由于某些基因突变而具有了生长优势,但这些基因突变也会成为肿瘤细胞的“练门”。del(17p)发生在10%的新发多发性骨髓瘤中,在复发病例中出现的机率还会更高。del(17p)在直肠癌中更为普遍,概率超过50%。因此,del(17p)可作为生物标记物来筛选病人,使ATAC药物选择加速审批通道成为可能。3.肿瘤细胞很难对鹅膏菌素产生耐药性。RNA聚合酶II是细胞生存必不可少的部件,没有冗余的蛋白或其它途径可以代替它。一旦RNA聚合酶II被抑制,肿瘤细胞只有死路一条。另外,鹅膏菌素也不会被MDR受体泵出细胞外。它会一直滞留在细胞内,直至细胞死亡,真正地“切断了所有后路”。当然,肿瘤细胞对ATAC药物还会产生耐药性,但它们只能从ATAC的抗体元件方面下手,比如通过抗原逃逸的方式、避免ATAC进入细胞而躲过一劫。4.ATAC的杀伤作用可进一步激活抗肿瘤的免疫活性。由于α-鹅膏菌素的脂溶性较差,它无法在杀完一个肿瘤细胞后再窜到相邻的肿瘤细胞中起作用(“旁观者效应”,bystandereffect)。但它的较弱的旁观者杀伤效应可以被较强的触发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的功能来弥补。ICD将唤醒原本被蒙蔽住的免疫系统,使其认清肿瘤的真面目,让其对肿瘤细胞发起全面进攻。能引起ICD的ADC偶联的小分子化合物十分难得,比如MMAE有较强的ICD效应,而Maytansine和Camptothecin的就比较弱。由于α-鹅膏菌素较强的ICD效应,ATAC和anti-PD-(L)1联合用药或许会产生强协同效应。HeidelbergPharma的第一个ATAC药物已进入一期临床试验。如果它最终被证明安全有效并获批上市,我们的世界就又多了一个毒素衍生的药物。药物研发的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一个治病救命的神奇药物的产生,也许可以溯源到历史上的一起中毒事件,也许是因为多年以前曾有人多问了一句whatif。参考资料(上下滑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feijia.com/sfjjn/10072.html
- 上一篇文章: 别挤了辉瑞新冠药欧日韩供远大于求,强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